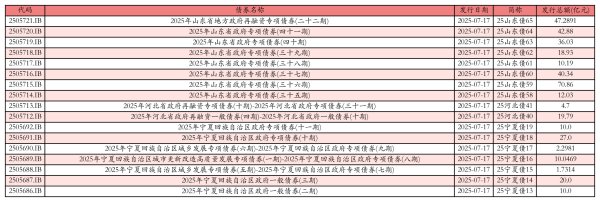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…节选凯丰配资
韩愈
孤臣昔放逐,血泣追愆尤。汗漫不省识,恍如乘桴浮。
或自疑上疏,上疏岂其由。是年京师旱,田亩少所收。
上怜民无食,征赋半已休。有司恤经费,未免烦征求。
富者既云急,贫者固已流。传闻闾里间,赤子弃渠沟。
持男易斗粟,掉臂莫肯酬。我时出衢路,饿者何其稠。
亲逢道边死,伫立久咿嚘。归舍不能食,有如鱼中钩。
适会除御史,诚当得言秋。拜疏移閤门,为忠宁自谋。
上陈人疾苦,无令绝其喉。下陈畿甸内,根本理宜优。
积雪验丰熟凯丰配资,幸宽待蚕麰.天子恻然感,司空叹绸缪。
谓言即施设,乃反迁炎州。同官尽才俊,偏善柳与刘。
展开剩余89%韩愈的《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…》是一首兼具叙事、抒情与议论的长篇古诗,节选部分以自传式的笔触,记录了他因直言进谏而遭贬谪的经历,字里行间满含对民生疾苦的悲悯、对忠而被贬的愤懑,也暗藏了与柳宗元、刘禹锡的深厚情谊。以下从诗歌解析、韩愈心路、韩柳刘交游故事三方面展开:
一、诗歌节选解析:以 “贬谪” 为线,串联民生与忠直
节选部分可分为 “忆贬谪之由”“述民生之苦”“抒进谏之忠”“叹贬迁之愤”四层,逻辑清晰,情感层层递进:
1. 开篇:贬谪后的迷茫与自我叩问
“孤臣昔放逐,血泣追愆尤。汗漫不省识,恍如乘桴浮”,开篇以 “孤臣” 自喻,点明自己被贬的处境 ——“放逐” 后独自落泪反思 “愆尤”(过错),却只觉 “汗漫”(茫然),像乘木筏漂泊无依。这种迷茫并非真的自认有错,而是对 “为何被贬” 的困惑,为后文揭示进谏背景埋下伏笔。
“或自疑上疏,上疏岂其由” 进一步强化困惑:他怀疑被贬是因 “上疏”(上奏章),却又不愿相信 —— 自己的进谏本是为民生,怎会成为贬谪的理由?
2. 核心:铺陈京师旱灾的民生惨状
这部分是韩愈进谏的 “事实依据”,也是全诗最具感染力的段落,以白描手法展现灾难下的人间疾苦:
顶层政策与底层执行的矛盾:“是年京师旱,田亩少所收。上怜民无食,征赋半已休。有司恤经费,未免烦征求”—— 皇帝本已怜悯百姓,下令减免一半赋税,但地方官吏为 “体恤经费”,仍强行搜刮,政策到基层完全走样,凸显官僚体系的腐朽。 贫富差距与百姓绝境:“富者既云急,贫者固已流。传闻闾里间,赤子弃渠沟”—— 连富人都感到窘迫,穷人更是流离失所;民间竟有 “赤子(婴儿)弃于渠沟” 的惨剧,将民生疾苦推到极致,触目惊心。 卖子求生与人性冷漠:“持男易斗粟,掉臂莫肯酬”—— 百姓为换一斗粟米,竟要卖掉儿子,却仍无人肯怜悯;“我时出衢路,饿者何其稠。亲逢道边死,伫立久咿嚘”—— 韩愈亲眼所见:路边饿殍遍地,他目睹有人死在道旁,只能长久伫立、呜咽叹息,个人的无力感与对百姓的悲悯交织。 自我共情:民生之痛刻入骨髓:“归舍不能食,有如鱼中钩”—— 目睹惨状后,韩愈连饭都吃不下,内心的痛苦像 “鱼被鱼钩勾住” 般煎熬,这也成为他后来 “上疏进谏” 的直接动因:百姓之苦已让他无法置身事外。3. 转折:进谏的初衷与被贬的结局
“适会除御史,诚当得言秋” 是关键转折 —— 韩愈恰逢被任命为监察御史(“御史” 主监察、进谏),认为自己肩负 “言责”,理应在 “得言秋”(可直言进谏的时机)为百姓发声。
“拜疏移閤门,为忠宁自谋。上陈人疾苦,无令绝其喉。下陈畿甸内,根本理宜优”,直白写出进谏的纯粹:他到閤门递上奏章,并非为自身谋利,而是 “为忠”—— 上陈百姓疾苦,恳请朝廷不要断绝他们的生路;下陈京城附近(“畿甸”)是国家根本,理应优先安抚,政策逻辑清晰,尽显 “以民为本” 的忠直。
然而结局却截然相反:“天子恻然感,司空叹绸缪。谓言即施设,乃反迁炎州”—— 皇帝本已被奏章打动,司空(古代高官,此处指宰相)也感叹他考虑周密,众人都以为政策会立刻实施,韩愈却反而被贬到 “炎州”(南方炎热偏远之地,此处指阳山,韩愈首次贬谪地)。这种 “预期与现实” 的巨大落差,将朝廷的 “忠而见弃” 刻画得淋漓尽致,也暗含韩愈的愤懑与无奈。
最后 “同官尽才俊,偏善柳与刘”,在贬谪的失意中,突然提及 “同官” 中的柳宗元、刘禹锡 —— 同朝为官的人皆是才俊,但他尤其与柳、刘交好,既为后文抒发与二人的情谊铺垫,也暗示:柳、刘与他一样,都是心怀理想、敢于直言的 “才俊”,三人的命运早已因共同的政治立场而绑定。
二、韩愈:从 “直言进谏” 看其 “文以载道” 的人格底色
节选诗歌本质是韩愈 “人格” 的缩影 —— 他的 “文” 始终为 “道” 服务,而 “道” 的核心是 “儒家的民本与忠直”:
对民生的悲悯:超越官僚的 “士人情怀”:作为官员,他本可对民生疾苦 “视而不见” 以自保,但他却将 “亲逢道边死” 的冲击刻入内心,甚至 “归舍不能食”,这种 “共情力” 源于儒家 “仁者爱人” 的底色,也是他区别于一般官僚的关键。 对忠直的坚守: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 的勇气:明知进谏可能触怒朝廷,仍坚持 “为忠宁自谋”,哪怕最终被贬 “炎州”,也未动摇 —— 这种 “不畏贬谪、敢于发声” 的态度,贯穿韩愈一生(后来他因反对唐宪宗迎佛骨,再次被贬潮州,仍写下《论佛骨表》直言劝谏)。 对友情的珍视:贬谪中的精神慰藉:在 “反迁炎州” 的失意中,特意提及 “偏善柳与刘”,可见柳、刘二人在他心中的分量 —— 他们不仅是同朝为官的 “同事”,更是志同道合的 “知己”,这种友情成为他贬谪生涯中的重要精神支撑。三、韩愈、刘禹锡、柳宗元的故事:志同道合的 “永贞革新” 群体
韩愈与柳宗元、刘禹锡的深厚情谊,源于他们共同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经历,核心围绕 “永贞革新” 展开,三人的关系可概括为 “志同道合 — 命运与共 — 隔世相望”:
1. 初识:科举与仕途的交集,奠定志同道合的基础
三人都出身中小地主家庭,均通过科举进入仕途(韩愈贞元八年中进士,柳宗元贞元九年中进士,刘禹锡贞元九年中进士),早年都曾在京城为官,且都对当时的社会问题(如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权、赋税苛重)有深刻认识,主张以儒家思想改革弊政,实现 “中兴”。
韩愈与柳宗元:虽后来因 “古文运动” 的某些观点有分歧(柳宗元更强调 “文以明道” 的 “道” 需兼顾现实,韩愈更强调 “儒家道统” 的传承),但核心都是反对六朝以来的 “骈文浮艳之风”,主张 “文以载道”,是 “古文运动” 的核心领袖(后世将二人并称为 “韩柳”)。 韩愈与刘禹锡:刘禹锡性格豪迈,才华横溢,与韩愈都擅长诗歌与散文,二人在京城为官时多有唱和,对民生疾苦的关注高度一致(刘禹锡后来也写下《观刈麦》等反映民生的诗歌)。2. 核心:“永贞革新”—— 共同的政治理想与命运转折
唐顺宗永贞元年(805 年),以王叔文、王伾为核心,柳宗元、刘禹锡为骨干的改革派,发起了 “永贞革新”,旨在打击宦官专权、藩镇割据,减轻百姓赋税,韩愈虽未直接加入改革核心,但他的政治主张(如减轻民生负担、整顿吏治)与革新派高度契合,且与柳、刘二人立场一致。
然而,“永贞革新” 仅持续 100 余天便失败(顺宗退位,宪宗即位,改革派被清算),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,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,史称 “二王八司马事件”—— 这是三人命运的重要转折点:
韩愈虽未被贬,但因曾为改革派发声,也受到排挤,后来因反对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; 柳宗元在永州写下《永州八记》《捕蛇者说》等名篇,借山水抒发抑郁,却始终未放弃对 “道” 的坚守; 刘禹锡在朗州写下《秋词》(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”),尽显豪迈不屈,即便后来多次被贬,仍保持乐观。值得注意的是,“永贞革新” 失败后,三人虽天各一方,但始终通过书信、诗歌传递情谊:韩愈曾写下《柳子厚墓志铭》,高度评价柳宗元的才华与人格,感叹他 “材不为世用,道不行于时”;刘禹锡则在柳宗元去世后,整理他的文集,让其思想与文学成就得以流传。
3. 终章:隔世的缅怀 —— 友情跨越生死
柳宗元于元和十四年(819 年)病逝于柳州(他被贬柳州刺史时,曾积极兴修水利、兴办学校,改善当地民生),年仅 47 岁。韩愈当时在潮州被贬,听闻噩耗后悲痛万分,写下《祭柳子厚文》,文中 “凡物之生,不愿为材;凡材之生,不愿为器;器之既成,患其不毁”,既是对柳宗元才华的惋惜,也是对他一生 “忠而被贬” 的愤懑。
刘禹锡则在柳宗元去世后,承担起照顾其家人的责任,并将柳宗元的诗文整理成《柳河东集》,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文学遗产。后来刘禹锡晚年回到洛阳,仍时常在诗中缅怀柳宗元与韩愈,如《重至衡阳伤柳仪曹》中 “忆昨与故人,湘江岸头别”,字里行间满是对旧友的思念。
韩愈的这首诗节选,不仅是他个人贬谪经历的记录,更是中唐时期知识分子 “以道自任” 的缩影 —— 韩愈、柳宗元、刘禹锡三人,虽命运多舛,却始终坚守 “为民发声、为道献身” 的理想,他们的友情因共同的理想而深厚,他们的文学与思想因 “忧国忧民” 而不朽。
从诗歌中的 “亲逢道边死” 到柳宗元的 “苛政猛于虎”凯丰配资,再到刘禹锡的 “沉舟侧畔千帆过”,三人用不同的笔触,书写了中唐知识分子的悲悯与坚韧,也为后世留下了 “士人之魂” 的典范。
发布于:河南省九牛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